辦入院、繳押金、安排病房,我獨自一人,不慌不忙地處理妥當。
公公躺在病床上,望著我忙前忙後,眼裡滿是感動與愧疚。
「小晚啊,又給你添麻煩了。」
「爸,您說啥呢,這都是應該的。」
我給他掖了掖被角:「您安心養病,啥都別想。」
趙翠也來了, 站在一旁手足無措,像個做錯事的孩子。
想幫忙卻不知從何下手,想說話又怕說錯。
我沒理她, 只顧專心照顧公公。
顧成第二天趕了回來, 風塵僕僕, 一臉焦急。
看到病房裡一切都被我安排得妥妥帖帖, 他愣住了。
走到我身邊,輕輕握住我的手。
「老婆, 辛苦你了。」
我搖搖頭:「爸也是我爸。」
他望著我, 眼裡情緒複雜。
晚上一同回家,路上他忽然問:「小晚, 為啥……爸生病,你這麼上心?」
我望著窗外倒退的街景,淡淡地說:
「因為自打進了這個家門,只有爸真心把我當一家人。」
「他會在你媽說我時幫我解圍,會在你沉默時嘆著氣拍拍我肩膀。」
「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丈。就這麼簡單。」
顧成握方向盤的手緊了緊,沒再說話。
但他一定懂了。
這份區別對待,是我給趙翠上的最後一課。
讓她明白,尊重和情分靠真心換來, 而非靠身份和規矩逼迫。
而她, 已永遠失去了換取這份真心的資格。
16
公公出院後, 家裡恢復平靜。
我和顧成的關係也在平靜中慢慢回暖。
我們開始像正常夫妻那樣, 一起看電影,周末去郊遊。
那份冷冰冰的借款協議被我鎖在保險柜最深處, 再也沒拿出來過。
但我們都知道它就在那裡,像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疤。
提醒著我們曾走過怎樣一段荒唐又殘酷的路。
半年後的冬天, 我生下了孩子。
是個男孩, 長得很像顧成。
孩子的到來給這個家帶來久違的笑聲。
趙翠想抱孫子,眼神里滿是渴望。
她會試探著伸手,又在我平靜的目光下默默縮回去。
我沒阻止, 也沒鼓勵。
她可以看, 可以逗,卻不能抱。
這是我無聲的規則。
有天我心血來潮,又買了盒頂級燕窩,在廚房慢火細燉。
香氣瀰漫了整個屋子。
燉了兩碗, 一碗端給看報紙的公公:「爸, 補補身體。」
公公笑得合不攏嘴。
另一碗我端著走到客廳, 坐在沙發上自己一勺一勺慢慢品嘗。
自始至終沒看趙翠一眼。
她坐在對面椅子上, 望著我, 望著我手裡的燕窩。
眼神從期盼到失落, 再到絕望。
最後低下頭,渾濁的眼淚一滴一滴落在粗糙的手背上。
AA 制早已結束, 但我們之間那筆關於情分的帳, 永遠也算不清了。
她在我心裡,被永遠劃在了支出那一欄,再也沒有收入。
而我和顧成, 帶著那道疤,還在繼續往前走。
或許,這就是生活。
(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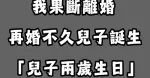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